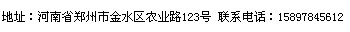喝茶的那些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大概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基本功课吧?!在退休前,一周二十多节课,即便是给每届外国学生讲中国茶文化讲得唾沫子飞,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也几乎没“茶”什么事儿。不是忙得泡杯茶的时间都没有,是怕喝了茶失眠。退休后,跟一群茶客有了些交往,跟着他们喝功夫茶,有点儿喜欢上了这种颇有仪式感的喝茶方式。搬到温江后,小区较偏僻,入住率很低,很长一段时间白天就我和儿子在家,除了柴米油盐酱醋,习琴种花读闲书之余,每天下午当炉涤器泡茶也成了一件事,总算凑齐了开门七件事,从职业妇女成功转型为家庭妇女。
在喝茶这事上,我的悟性不高,至今还停留在喜欢高香茶的水平,比如最喜欢的还是凤凰单枞和冻顶乌龙。这类香茶的香气不是外部添加的,而是由茶树生长的环境以及采摘炒制烘焙的功夫决定的。其次是兰花茶和茉莉花茶,这类香茶也称香片,是将春兰和茉莉的花瓣儿与绿茶一起窨制而成的。据说还有用珠兰、玫瑰、白兰花什么窨制的,没有喝过。自己倒是尝试过像《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样,在第一天开的荷花下午合苞前放入一小包茶叶,第二天清早开花时取出烘干,得到过一泡清香扑鼻的荷花茶。总之,对茶的感知还只在鼻舌之间,也就是只晓得香气和回甘。而人家资深茶客对茶的品鉴是能入喉入脏腑的,比如从存放多年而陈化的生、熟普洱中喝出顺滑、醇厚、喉韵、仓味儿之类岁月的味道,而我却很伤大雅地感觉是灰尘的味道。由此说明,在喝茶这事儿上,我就是图个新鲜的人。
曾听人说,苏轼被贬黄州,后又被招回。王安石写信给苏轼,让苏轼回程时给他带些长江中峡的水。苏轼欣然应允,结果船过中峡时,苏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忘了,直到下游才想起来。水流湍急,船回中峡不可能了。苏轼想:“都是一条江的水,有什么区别呢?”就让船工打了一壶下峡的水。当苏轼把水送给王安石,王安石把水煮开,泡了一壶阳羡茶后,肯定地说,这不是中峡水,而是下峡水。据说苏轼大惊,当然我也大惊,又特么这么神的人吗?这都能看出来。人家王安石的解释是引用《水经注》的,说是泡阳羡茶时,下峡水性黄味淡。中峡水急缓相当,浓淡适宜。而这杯茶好一会才泡出茶色。所以,一定是下峡水。书读得多,喝茶都喝得高人一筹。没读过《水经注》,不能印证。但是我始终对这个传说心存疑虑,携家带口那么远地带壶水,即便不怕洒了也不怕水馊了?再说,长江到了黄州那段早过了三峡,已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了,哪还有峡呢?《苏东坡传》里好像也没写这事儿呀,所以,传说还真不能轻信。
不过,读《陶庵梦忆》,明朝富二代张岱这个年轻时饱食终日,在吃喝玩乐上无所不用心其极的家伙是茶中高手则是无疑的。他创制的茉莉花茶名兰雪,力压当时的名茶日铸雪芽和休宁松萝,“一哄入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萝,止食兰雪”。甚而至于这两款名茶也自降身价冒兰雪之名出售。他在《闵老子茶》一文中写了与家住南京桃叶渡的一位年逾古稀的烹茶高手过招的过程,从茶种、产地、制法、春采还是秋采直到用什么泉的水,惠泉之水如何走千里不失清冽而磊生圭角,短短数百字栩栩如生,精彩纷呈。掩卷击案,真是让I服了You啊!不由得想到卢仝的《七碗茶》诗: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人家张宗子轻而易举就喝到第三碗的境界了。不过他家有钱啊,无锡惠山泉不渡钱塘,为喝泡茶,他大伯专雇西兴的挑夫挑水过江到杭州。这哪是我等讲究得起的过场啊!与之同朝的大画家徐渭也嗜茶,徐渭曾说:“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泉白石,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古人那也是真讲究啊!
与文人骚客比不得,我等小户人家,接一壶自来水,好歹也算活水。擢一撮一朵花拿来的茉莉花茶,大概五、六克,三块来钱吧,85到90度之间的水温冲下去,15秒出汤,感觉也与张宗子的兰雪茶“真如百茎素兰与雪涛并泄也”相差无几。水温出汤掌控好了,反复冲水十来泡也还唇齿留香。润润喉吻是完全没问题,若是呼朋唤友地来喝,破个孤闷也不是不能。
前些天在